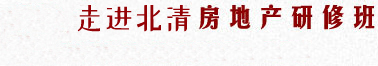
报名咨询热线:400-061-6586
当前位置:北京大学房地产研修班 >> 地产新闻 >> 浏览文章
未来10年,在中国买房还能赚钱吗?
发表时间:2016年07月25日 文章出处:金融智库-爱微帮 作者:佚名 浏览:
“逃离北上广”,这是一个近几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搁在大众眼前讨论一番的议题,这些核心城市的生活成本令为数不少的一部分人不堪负重。而不断上涨的房价,则令人有一种不真实的绝望感,工资再涨也跟不上房价。
笔者也常常有这样的疑问,房价现在这么高,还会再涨吗,以后会不会跌了?
不管有钱没钱,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。有能力做房产投资的人问的是以后买房子还能赚钱吗?而暂时买房吃力的人问的则是,未来买房会不会越来越困难?
如果我们将城市的房价放在一个分析框架中,就会发现它在短期受到资金、库存和政策决定,但从长期来看,则是一种人口趋势与产业结构的产物。它和城市化进程相伴而生,那些人口增加最快的地区、城市化最迅速、产业结构最符合需求的阶段,房价都是高企并且不断向上的。
美国城市地理学家纳瑟姆(Ray Northam)研究了当时已完成城市化国家的经验后,在1979年揭示了一条简明但深刻的规律: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大致都经历了类似正弦曲线上升的过程。这条曲线被命名为“纳瑟姆曲线”。
这其中有两个关键节点,即城市化率达到30%和70%。
城市化水平超过30%时,这个国家将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,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,人口快速涌进城市。当城市化达到70%左右后,第二个拐点出现,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进入平缓发展阶段。
中国城市化率在1998年前后达到第一个拐点,在那之前,中国只有不到30%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。这个拐点适逢房地产市场商业化,之后是波澜壮阔的房地产黄金十年。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,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6.1%,也还在加速城市化进程中,远远没有达到第二个拐点。
但“逃离北上广”给我们提了一个醒,“纳瑟姆曲线”揭示的城市化规律,并非一种单一的进程,这其中是分为两个阶段的。如果我们去了解美国、日本、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历史,就可以充分发现这一点。
第一阶段,城市化率30%-50%,农村人口涌入城市。这是一种潮水漫灌式的全面“入侵”,所有人都往城市迁移,不管大城市还是小城市,而全国中小城市的数量明显多于大城市,因此大部分人其实是去了中小城市。
很多80后的小伙伴都有这样的经历,他们在90年代和00年代这两个十年间,从农村随父母举家迁往左近的小城镇,他们后来有一些上了大学留在大城市了,有一些毕业后则回到了自己的小镇上。
在这个阶段,商品需求大于供给。一旦某一样新产品在大城市中被开发出来,很快就被复制到周边中小城市,有的甚至复制到全国,这种复制有的时候是企业主动采取的市场扩张,有的是被动的,被竞争对手模仿了。也正是因此,全国所有的中小城市都以发展制造业为优先考虑,创造庞大的就业机会,人口迅速向就近的中小城市靠拢,中小城市迅速发展起来。
这个过程中,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房价同步增长。大城市的房价,尽管从绝对值上看十分夸张,比如北京从3千上涨到了3万。但是从相对比例上看,中小城市的房价可能也不遑多让,从几百上涨到几千,10倍也比比皆是。
笔者有一位朋友A,居住在杭州附近的小城市,她父母带着她从农村出来,在1999年以600元/平米的价格购买了小镇上的一套房子,现在,这套房子的价格在7000-8000元/平米,十五六年涨了十几倍。同一时间段内,作为区域中心的杭州房价,涨幅最多也就是如此。这是一个全国房价普涨、“闭着眼买套房子都能赚到钱”的年代。
但当城市化率占比大约达到50%左右,变化来了。
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后,商品产能开始过剩,制造业在贡献经济增长的首要地位让位于第三产业,而服务业需要建立在大规模人口聚集基础上。这时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区分就出来了,人口众多的大城市,在三产上能够提供中小城市提供不了的服务。
笔者的朋友B,来自于一个三四线小城市,他去年为了女友辞掉了北京的工作来到杭州。不久他抱怨,杭州周末的各种社群活动和文化活动相比于北京,差了不止一个量级。抱怨完,他也说算了算了,杭州还算不错了,毕竟比他老家还是好多了。他回到老家就发现,周末除了约老同学打打游戏打打球,实在也没有什么活动。
到了这个阶段,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开始显现出来,全国人口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迁移,一个省份内的人口向省会或副省级城市迁移。
随着人口趋势的背离,再加上产业结构上的区别,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房价也开始分流。上半年楼市很火的时候,有一次去物业,一家人正在办理手续,笔者听到这一对为子女支付了首付的60后夫妻无奈地表示:“在老家卖掉一套房子,到杭州还不够付首付”。这种情况或许会越来越常见,但高房价也会让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年轻人不堪负重逃离。
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为56%,达到50%则是在2010年左右,“逃离北上广”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大规模讨论,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。
在个人的投资理财上,这是一种必须要留意的历史性转折。过去十几年随意买房子的行为应该停止了,但如果说买房子不赚钱了也不尽然,只是具备投资价值的不动产相比于从前十几年减少了,在做房产投资上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。
当我们考虑城市时,我们明白,人口净流入、三产占比不断提升、资金最多、施政效率高、土地供给合理的城市房价显然更有潜力。
而当涉及具体的某一套房子,哪些地段更好、哪些开放商显然更令人放心、怎么样的户型最好、如何装修更加实用等等,更是需要好好花时间去思考与学习的。
来源:吴晓波频道,本文已获得吴晓波频道授权,推荐关注财经第一自媒体-吴晓波频道。
延伸
新华社评楼市变局:繁荣景象背后潜伏着风险
继二线楼市“四小龙”中的合肥7月1日实施楼市新政之后,7月15日起厦门市也调整住房信贷政策,两地政策核心都是提高二套房及以上最低首付比例,释放出降低信贷杠杆为楼市降温的重要信号。
有所行动的不单是合肥和厦门。上海、深圳和北京限购政策不松绑;苏州、南京先后出台土地拍卖的“熔断机制”防过热;部分银行也开始通过“降杠杆”控制投资楼市的风险,如兴业银行大幅收缩开发贷款、个人按揭贷款额度,工行个人商用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50%调整至70%……
楼市再现降温信号,是对当前部分一二线城市再现过热苗头的警示。
今年上半年,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以及合肥、南京、苏州、厦门等核心二线城市轮番上演“日光盘”和“一房难求”剧情,将楼市热度急剧推高。房价上涨使得一二线城市库存压力基本释放,但“买涨不买跌”的心理驱使一波又一波买房人涌入售楼处,提早释放购房需求。上海、深圳再现通宵排队买房,合肥、南京陷入上万人争抢百套房源的疯狂模式……
繁荣景象的背后潜伏着风险。
与前几轮楼市反弹不同的是,本轮部分城市房价暴涨、地王频出,更多与金融杠杆的撬动有关。30%的首付将房地产投资的杠杆率上升到两倍以上,而年初曝出的链家和很多P2P公司提供的首付贷则进一步放大了杠杆,这一现象与2015年股市流失的场外配资非常相似。
加杠杆无疑有助于消化房地产库存,但如果杠杆过高,房地产就不再像必需品,而是越来越像金融品,势必催生房地产投机行为和房地产价格泡沫。如果继续加杠杆,将导致旧的泡沫还没挤出,新的泡沫又会积聚,最终可能会在政策收紧时破裂,导致房地产市场、金融体系甚至整个经济出现风险。
历史告诉我们,美国的次贷危机、日本的房地产泡沫,就是由于反复加杠杆,通过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、再宽松,形成了恶性循环。因此一旦发现房地产过度杠杆化的苗头,就必须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防范住房金融风险,关键要继续实施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,并加快相关领域改革,以便释放更多合理的新需求,并调整供给以匹配新需求。针对下半年和明年可能出现的市场短期调整,宜采取“细水长流”的调控策略,不宜“频施一揽子猛剂”,把握好货币、财税、土地等政策的出台时机、节奏和力度,协调搭配,保持调控有“温度”可持续。
防范住房金融风险,重点要贯彻执行好“因城施策”的调控主任务,同时要求城市间调控协同配合。既要分城施策,一二线与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应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措施;又要协同作战,作为风向标,要保持一二线城市市场平稳,防止一二线城市过度冷热,带动三四线城市去库存,确保住房市场长期可持续稳健发展。
来源:综合自新华社、微信公众号——吴晓波频道
转自:http://www.aiweibang.com/yuedu/134653473.html
笔者也常常有这样的疑问,房价现在这么高,还会再涨吗,以后会不会跌了?
不管有钱没钱,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。有能力做房产投资的人问的是以后买房子还能赚钱吗?而暂时买房吃力的人问的则是,未来买房会不会越来越困难?
如果我们将城市的房价放在一个分析框架中,就会发现它在短期受到资金、库存和政策决定,但从长期来看,则是一种人口趋势与产业结构的产物。它和城市化进程相伴而生,那些人口增加最快的地区、城市化最迅速、产业结构最符合需求的阶段,房价都是高企并且不断向上的。
美国城市地理学家纳瑟姆(Ray Northam)研究了当时已完成城市化国家的经验后,在1979年揭示了一条简明但深刻的规律: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大致都经历了类似正弦曲线上升的过程。这条曲线被命名为“纳瑟姆曲线”。
这其中有两个关键节点,即城市化率达到30%和70%。
城市化水平超过30%时,这个国家将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,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,人口快速涌进城市。当城市化达到70%左右后,第二个拐点出现,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进入平缓发展阶段。
中国城市化率在1998年前后达到第一个拐点,在那之前,中国只有不到30%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。这个拐点适逢房地产市场商业化,之后是波澜壮阔的房地产黄金十年。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,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6.1%,也还在加速城市化进程中,远远没有达到第二个拐点。
但“逃离北上广”给我们提了一个醒,“纳瑟姆曲线”揭示的城市化规律,并非一种单一的进程,这其中是分为两个阶段的。如果我们去了解美国、日本、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历史,就可以充分发现这一点。
第一阶段,城市化率30%-50%,农村人口涌入城市。这是一种潮水漫灌式的全面“入侵”,所有人都往城市迁移,不管大城市还是小城市,而全国中小城市的数量明显多于大城市,因此大部分人其实是去了中小城市。
很多80后的小伙伴都有这样的经历,他们在90年代和00年代这两个十年间,从农村随父母举家迁往左近的小城镇,他们后来有一些上了大学留在大城市了,有一些毕业后则回到了自己的小镇上。
在这个阶段,商品需求大于供给。一旦某一样新产品在大城市中被开发出来,很快就被复制到周边中小城市,有的甚至复制到全国,这种复制有的时候是企业主动采取的市场扩张,有的是被动的,被竞争对手模仿了。也正是因此,全国所有的中小城市都以发展制造业为优先考虑,创造庞大的就业机会,人口迅速向就近的中小城市靠拢,中小城市迅速发展起来。
这个过程中,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房价同步增长。大城市的房价,尽管从绝对值上看十分夸张,比如北京从3千上涨到了3万。但是从相对比例上看,中小城市的房价可能也不遑多让,从几百上涨到几千,10倍也比比皆是。
笔者有一位朋友A,居住在杭州附近的小城市,她父母带着她从农村出来,在1999年以600元/平米的价格购买了小镇上的一套房子,现在,这套房子的价格在7000-8000元/平米,十五六年涨了十几倍。同一时间段内,作为区域中心的杭州房价,涨幅最多也就是如此。这是一个全国房价普涨、“闭着眼买套房子都能赚到钱”的年代。
但当城市化率占比大约达到50%左右,变化来了。
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后,商品产能开始过剩,制造业在贡献经济增长的首要地位让位于第三产业,而服务业需要建立在大规模人口聚集基础上。这时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区分就出来了,人口众多的大城市,在三产上能够提供中小城市提供不了的服务。
笔者的朋友B,来自于一个三四线小城市,他去年为了女友辞掉了北京的工作来到杭州。不久他抱怨,杭州周末的各种社群活动和文化活动相比于北京,差了不止一个量级。抱怨完,他也说算了算了,杭州还算不错了,毕竟比他老家还是好多了。他回到老家就发现,周末除了约老同学打打游戏打打球,实在也没有什么活动。
到了这个阶段,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开始显现出来,全国人口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迁移,一个省份内的人口向省会或副省级城市迁移。
随着人口趋势的背离,再加上产业结构上的区别,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房价也开始分流。上半年楼市很火的时候,有一次去物业,一家人正在办理手续,笔者听到这一对为子女支付了首付的60后夫妻无奈地表示:“在老家卖掉一套房子,到杭州还不够付首付”。这种情况或许会越来越常见,但高房价也会让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年轻人不堪负重逃离。
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为56%,达到50%则是在2010年左右,“逃离北上广”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大规模讨论,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。
在个人的投资理财上,这是一种必须要留意的历史性转折。过去十几年随意买房子的行为应该停止了,但如果说买房子不赚钱了也不尽然,只是具备投资价值的不动产相比于从前十几年减少了,在做房产投资上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。
当我们考虑城市时,我们明白,人口净流入、三产占比不断提升、资金最多、施政效率高、土地供给合理的城市房价显然更有潜力。
而当涉及具体的某一套房子,哪些地段更好、哪些开放商显然更令人放心、怎么样的户型最好、如何装修更加实用等等,更是需要好好花时间去思考与学习的。
来源:吴晓波频道,本文已获得吴晓波频道授权,推荐关注财经第一自媒体-吴晓波频道。
延伸
新华社评楼市变局:繁荣景象背后潜伏着风险
继二线楼市“四小龙”中的合肥7月1日实施楼市新政之后,7月15日起厦门市也调整住房信贷政策,两地政策核心都是提高二套房及以上最低首付比例,释放出降低信贷杠杆为楼市降温的重要信号。
有所行动的不单是合肥和厦门。上海、深圳和北京限购政策不松绑;苏州、南京先后出台土地拍卖的“熔断机制”防过热;部分银行也开始通过“降杠杆”控制投资楼市的风险,如兴业银行大幅收缩开发贷款、个人按揭贷款额度,工行个人商用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50%调整至70%……
楼市再现降温信号,是对当前部分一二线城市再现过热苗头的警示。
今年上半年,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以及合肥、南京、苏州、厦门等核心二线城市轮番上演“日光盘”和“一房难求”剧情,将楼市热度急剧推高。房价上涨使得一二线城市库存压力基本释放,但“买涨不买跌”的心理驱使一波又一波买房人涌入售楼处,提早释放购房需求。上海、深圳再现通宵排队买房,合肥、南京陷入上万人争抢百套房源的疯狂模式……
繁荣景象的背后潜伏着风险。
与前几轮楼市反弹不同的是,本轮部分城市房价暴涨、地王频出,更多与金融杠杆的撬动有关。30%的首付将房地产投资的杠杆率上升到两倍以上,而年初曝出的链家和很多P2P公司提供的首付贷则进一步放大了杠杆,这一现象与2015年股市流失的场外配资非常相似。
加杠杆无疑有助于消化房地产库存,但如果杠杆过高,房地产就不再像必需品,而是越来越像金融品,势必催生房地产投机行为和房地产价格泡沫。如果继续加杠杆,将导致旧的泡沫还没挤出,新的泡沫又会积聚,最终可能会在政策收紧时破裂,导致房地产市场、金融体系甚至整个经济出现风险。
历史告诉我们,美国的次贷危机、日本的房地产泡沫,就是由于反复加杠杆,通过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、再宽松,形成了恶性循环。因此一旦发现房地产过度杠杆化的苗头,就必须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防范住房金融风险,关键要继续实施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,并加快相关领域改革,以便释放更多合理的新需求,并调整供给以匹配新需求。针对下半年和明年可能出现的市场短期调整,宜采取“细水长流”的调控策略,不宜“频施一揽子猛剂”,把握好货币、财税、土地等政策的出台时机、节奏和力度,协调搭配,保持调控有“温度”可持续。
防范住房金融风险,重点要贯彻执行好“因城施策”的调控主任务,同时要求城市间调控协同配合。既要分城施策,一二线与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应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措施;又要协同作战,作为风向标,要保持一二线城市市场平稳,防止一二线城市过度冷热,带动三四线城市去库存,确保住房市场长期可持续稳健发展。
来源:综合自新华社、微信公众号——吴晓波频道
转自:http://www.aiweibang.com/yuedu/134653473.html